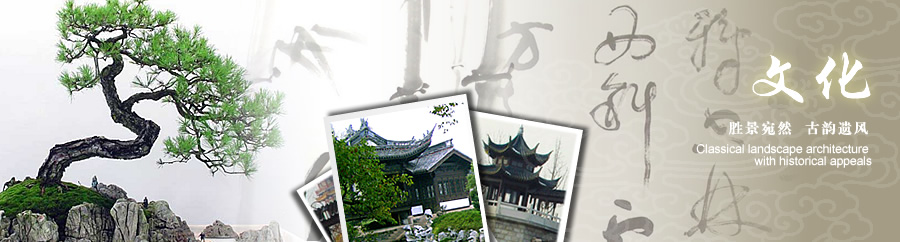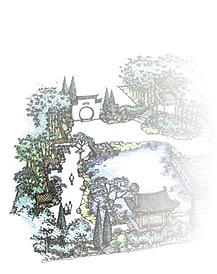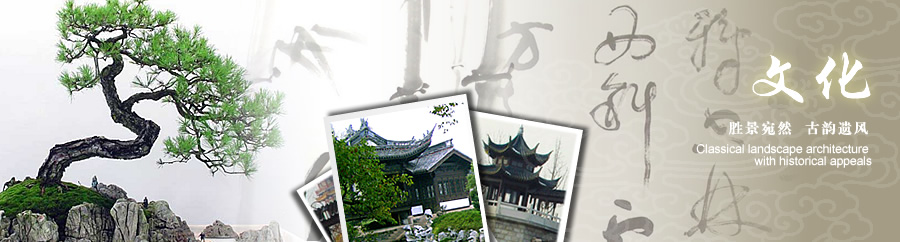|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五月的北京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春意盎然,郁郁葱葱,百花盛开。用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这首《赏牡丹》来描写这般美景亦可谓贴切。更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五月中国美术馆的一件展事也应时体现了这句古诗的核心“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件展事就是“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
五月八日开幕式上名流云集、规模可谓盛况空前。一进中国美术馆一楼大门,正对的墙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冯其庸先生的山水画为背景,赫然映照着由章太实大师唯一在世的弟子、著名诗人、山西大学教授、百岁老人姚奠中先生所书:“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的醒目标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原校长纪宝成,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国家文物局原总工谢辰生等一批学术界、艺术届名流以及冯老的“粉丝”道友等几百人参加了开幕式。
展览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等在冯老的陪同下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本次展览。
冯老上一次在2006年5月下旬中国美术馆的书画展,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了。对照上次书画展的展品,虽然已经走过六整年,本次作品有明显不同并且特点突出:立意鲜活、生机盎然、宏阔大气、品质高尚。
“百幅溢尺诗书画,挥毫辛卯壬辰间;汉武钦点嵩阳栢,铺纸溢丈拔笔端”。本次展出的大部分作品,大多以冯老八十九至九十岁所作的溢尺幅作品居多。比如:高5.8米,宽2.15米的《嵩阳古松》之力作堪称冯老九十岁高龄时绘出的扛鼎之作。以一棵千年古柏为表现对象,气象非凡。古柏现存于嵩山嵩阳书院,据说汉武帝东巡时曾见此树。
“诗如太白与杜甫,书自二王榜字坚,画追大痴宋元意,敲醒书圣与诗仙,崇古诗情书画意,黄山顶松总参天”。这几句诗是我对冯老诗书画的欣赏之体会的概括。冯老的诗词功底可谓深厚,尤其唐诗底蕴更加深厚。在多数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中的题诗可略见一斑。其中在《嵩阳古松》画中题诗:“汉武东巡事已陈,马迁史笔久封尘。嵩阳老柏今犹在,青眼看人万世情。汉唐盛世亲经历,又见东方出五星。昨夜嫦娥奔月府,红旗永驻九天青”。在另一幅青绿山水图《瞿塘峡》题诗:“十年不到瞿塘峡,梦里常存白盐山。想得雄关高万丈,轻舟已逝胆犹寒”。
冯老的书法力作亦是空前之壮观,所书之内容均自题之诗句。所书之作品多以大横幅、大长联为主,所书之字幅多以“榜书”大字之出奇。驻足在冯老之巨幅书作前,冯远先生概括冯老之书法“小字出自二王”,大字已自成一体之“榜书”。
冯老画山水一直以沿袭宋元风格而著称。本次的展品中,冯老仍以深厚古朴的宋元风格画作为主流,八十九至九十岁间又临摹了大量溢尺宋元名家作品,如临元代黄公望(号“大痴”)等的《山居图》、《听瀑图》、《水阁山村图》以及《深山读书图》也在本次展出。冯老所临作品之笔法之意境公认为极致。
“重彩绘罢西域地,大漠孤烟现重关”冯老是考证型学者,多次登上帕米尔高原, 在年近八旬时终于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重新发现并确认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并立碑,曾轰动中外佛学界。这是冯老人生中对学问锲而不舍,孜孜以求除红学研究外的所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一笔,用原学会会长赵朴初的话说:你解决了我们佛学界所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
近20年间,冯其庸走访新疆十余次,其中三次走上帕米尔高原,两次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在10年前,他穿越了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考察楼兰古城。冯老曾有兴致地讲过自己考察玄奘取经东归长安最后路段的经历,并坦率地说:“我的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重走玄奘之路,除了想验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西域风光也吸引着我。我希望能够亲身领略唐代诗人们在诗句中所描绘的雄伟而绮丽的自然风光。本次画展中冯老“以彩代墨”的多幅绘画作品,将西部山水描绘的畅快淋漓。”
“冯老九十高龄,以彩代墨,作品宏阔大气,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实属不易,堪称我们之楷模”。这是我与好友雕塑家纪峰先生陪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观展时,冯远先生的赞誉之词,可谓贴切之至。
综上简述仅为冯老的诗词、书法、绘画的一部分,仅为其红学、佛学、戏剧等学术领域成就的冰山一角,纵观冯老的半个多世纪辛劳苦究换来的学术成果,著名的“南饶北季”均对他赞赏有加,饶宗颐老先生经常为他的画集等作序。他与不同领域的大家成为知己,如:与贝聿铭、杨宪益、陈从周、杨仁恺、许麟庐、启功、徐邦达、任继愈、王世襄等的友谊,他在《瓜饭集》等著作中均有所描述。冯老是“南饶北季”之后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著名狂草艺术家、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金融文联名誉主席、中国美术馆顾问唐双宁为其本次诗书画展题写了:“一代宗师”。我认为冯老名至实归。 实可谓:“博大精深国学事,当代几人能比肩,无数苦究寡眠夜,黑发换做宗师冠”。
拜谒冯老已近十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我与冯老的密切程度,已成忘年之交。可以说:“天赐恩翁惠顾我,数载教诲恩般般”。
我对冯老的学识、为人、品质等可谓顶礼膜拜;其治学、敬业态度的严谨,自重、努力、扎实更令我等晚辈折服。冯老在做人方面对我经常引经据典、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这位当今大儒对我人生规划的校正,世界观的改造,人生的感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冯老对我在书法绘画深入研习可谓不吝赐教,从书法作品创作的章法布局到深入研习过程中的选帖、选纸、用墨、印章使用,装裱之规矩,甚至毛笔的清洗方法都详细入微指导。
除书法绘画外,我也喜欢收藏字画,记得去年夏季我在浙江出差,偶然机会收到一幅苏州著名画家蒋风白先生(冯老的老朋友)的兰竹,把握不准,请冯老掌眼,他老人带病讲解这幅作品的特点,并为我捡漏高兴,病好些后有欣然为我在这幅作品上题签说明。诸如此类,我经常请教他老人家,他的悉心教导令我感动不已。
我转行从事园林规划设计、施工,企业管理已近八年。从园林基本知识的不断学习实践到对园林艺术的深刻理解,是每个热爱园林职业者必经之路。冯老对我的工作也很关心,与他老人家交流时,他经常嘱咐我,多看陈从周先生的书。陈先生是古建园林界的大师级人物,因此,我拜读了他的《说园》、《梓室说园》、《陈从周园林随笔》、《园林谈丛》等很多著作。对我园林艺术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界开阔了,工作起来也相对得心应手了。
对我更深一层的影响是冯、陈二老的学术崇拜。冯老从1942年开始就与陈老结识,是多年挚交,陈先生的多数著作均由冯老作序。二老均为教授出身,学养深厚,均师从过诗人、书法家国学大师王遽常。冯老文学著作等身、为国学大师;陈老作为文学家,解放前就出版《徐志摩年谱》等文学著作,作为园林古建专家,园林古建专业著作颇丰,对园林古建界的学术贡献亦非凡。
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的设计方案,就出自陈老之手。
他是张大千的关门弟子,当年张大千在苏州网师园的租住绘画的地方,就是院中的“殿春移”,这里是公认的园林古建小院的“极致”,是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瑰宝之一。而“明轩”就是其翻版。可以想象出陈老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最直接的感悟是,作为我公司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个援外施工项目“明轩”,以它古朴典雅的苏式古典园林特色,成为了海外园林建筑史上一块里程碑,不禁为此而自豪。
德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席勒曾说过: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这就是审美教育的任务。正是冯老先生这种求真问美的治学态度,无形中教诲了我:作为一名追求艺术真谛的园林工作者,须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寻道问源”之心,方能得大智慧,于无意间得大成。
回首近十年来所走过的路,能够结识冯老并承蒙他多方引导、教诲和启发,是我人生之大幸。我时常怀揣感恩之心回想他老人家的每一次教导,在冯老崇高人性光辉的指引下,使我在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都能步履坚实、从容不迫。在当今浮躁风盛、宁静难寻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人对艺术的推崇远不及对金钱的追求,对道义的信守远不及对势利的看重……面对这些,我却从冯老身上找了所谓人生的答案。人的一生要想活得坦坦荡荡,只有心中有爱、有他人、有社会、有责任,正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观赏完冯老九十诗书画展,走出中国美术馆,夏日的阳光斜照过来,淡淡的,和微风交织在一起,柔柔地拂过身旁,让人心旷神怡。在感到心中笃定的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前行的力量。
作者:孙满成
现为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原载于《中国建筑装饰报》,节选于《中国建筑报》
|